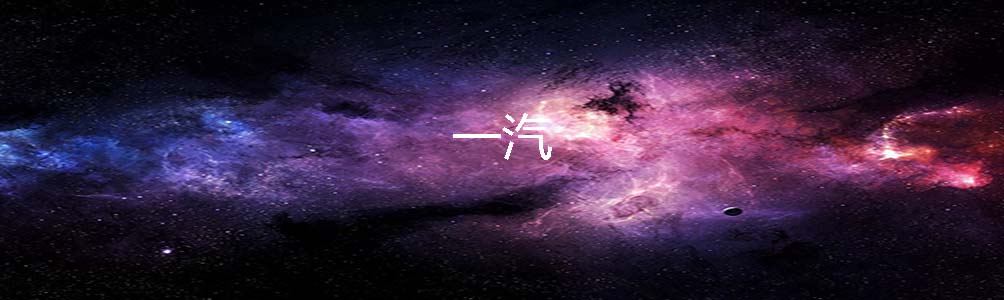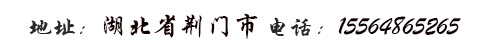今天向一汽老厂长黄兆銮告别
|
行政求职招聘QQ群 https://www.edunews.net.cn/2021/ywbb_0912/131570.html原一汽厂长黄兆銮于年10月23日13时15分在长春因病辞世,享年91岁。《汽车商业评论》特意刊出年对他的口述历史访谈,以此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中国老汽车人。《汽车商业评论》记者葛帮宁编者按:今天(10月27日)上午9时01分,原一汽厂长、一汽集团咨询委员会主任黄兆銮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长春市龙峰殡仪馆忠孝厅举行。4天前,也就是10月23日13时15分,他因病逝世,享年91岁。在一汽集团,黄兆銮的好人缘远近闻名。跟他交流,没有丝毫压力。偶尔走在一汽的厂区里,甚至去附近超市购物,人们都习惯性地称他“黄厂长”—他身上却找不到一点厂长的架子。这位年出生的老汽车人,祖籍广东南海,天津长大。工作两年后考上北洋大学机械系,上学3年后加入林彪的南下工作团,却被抽调到叶剑英的华南工作团到广东工作。年,国家要求技术干部归队转工业,他成为二汽筹备组成员,被刘西尧派到一汽实习时,被孟少农的一句话“留”了50年。年,黄兆銮到苏联实习工具管理,回国后,他在工具厂一干就是25年,成为我国汽车工业第一代工具管理的创始人。他在采访中对我强调:“你说工具我还略知一二,工具是个牙齿,啃零件的,我没搞过产品,所以我是个不懂汽车制造的汽车制造厂厂长。”年1月,他任一汽副厂长,年8月任常务副厂长,年3月任代理厂长,同年7月担任厂长。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徐元存先后在工具分厂和一汽总厂两度搭班子共事。这在一汽50多年的历史中,绝无仅有。年6月,黄兆銮离休,耿昭杰接任。退下来后,耿昭杰让他当顾问。他说,我给你当个伙计,你怎么说,我怎么干。他还说,一个人有一个打法,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我有个原则,就是不参与,不干预,更不干扰。黄兆銮从年一直“顾问”到年,当年一汽咨询委员会成立,12个人进入咨询委,他是主任。年9月的一个下午,86岁的黄兆銮在长春家里接受《汽车商业评论》口述历史访谈,他用生动的表情,爽朗的笑声,诙谐的语言,将我们引入到一个久远的热情澎湃的年代。今天,《汽车商业评论》特意刊出年的口述采访,以此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中国老汽车人。我是广东南海人,为了谋生父母到天津工作,我就生长在天津。年高中毕业时,父亲从铁路局失业,我的两个哥哥在抗战前就去了昆明,日本鬼子打进来后,没办法通信,钱也寄不来,所以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就出来找工作。起初,我在天津会计函授学校当办事员。这个函授学校共3人:校长和教员是一人,把门的是他父亲。所谓办事员,什么都干,学生函授或者答题,我就刻钢板,给人复信。工资也不高,只有几十块钱。干了不到一年,我想,我一个高中生,成天干这个,也不行啊,就去了一个做肥皂的工厂。后来我知道这里不光做肥皂,还做化学药品。因为在高中学过化学,我就在化验室当助理技师。这个工厂也不大,有20个工人,厂长是日本人。我这个技师要参加生产,上大锅做肥皂。工资比函授学校高点,中午还能管顿饭。半年后,抗战紧张起来,日本征兵时把厂长征走了,工厂也就黄了。正好我也不愿意在这里干,就失业了。但家里总得生活,我这点工资虽然不多,还可以补助一下。于是我就去当家庭教师,每周去几次,去一次给一次钱,主要教初中生的数学、英文—我中学念的是个教会学校,老师都是英国人,所以外语还不错。一两个月后,唐山开滦矿务局招人,它是跟英国人合办的。我去报考,但进去很难,那时也兴“走后门”,我没后门可走,没有被录取。开滦那里还有个学校,要成立工务员训练所,专门招中学生和高中生。所谓工务员,现在叫技术员,英文是foreman,就是技术领班,工厂车间里除了工长以外的技术领班。我报名参加考试,这次考上了。在训练所机械系里学习了一年半,算是半工半读,学校不交学费,还包吃包穿包住,并给点零花钱。学的大部分是大学课程,如电工原理、机械原理等。老师呢,一个留美的,一个留英的。毕业后,我被分到开滦唐家庄矿当技术员,相当于中级职员,管几个火车头。大约是年,抗日战争还没胜利,唐家庄矿既有日本人,又有英国人,矿长是比利时人。日本人占领中国后,开滦也被占了,外国人走了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工人老闹罢工、闹工资,我的群众关系不错,经常跟工人打成一片。我在开滦干了两年。我有个弟弟,比我小3岁,比我先上大学。我在开滦工作,除了补给家里生活,还供弟弟上大学,他读的是燕京大学机械系。我的工资说不清楚是多少钱,一个月给两袋白面和一袋苞米面,拿这些变成钱。年抗战胜利,我的两个哥哥跟家里取得了联系。他们觉得我学习成绩不错,就说,你别工作了,干脆还是上大学去吧。我也不好直接跟领导说要去考大学,一来他可能不同意,二来他同意了,就等于我被解雇了,我还得留点后路,要是考不上大学,也还有个饭碗。所以我就偷偷回天津去报名,报考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报纸一放榜,两个学校都考上了。这两个学校都很有名,北洋大学有多年的历史。我在训练所学习时的校长,他原是北洋采矿系的教授,也是广东人,他对我说,上北洋大学吧,全公费。再加上我的家在天津,生活比较方便,所以我就报了北洋大学机械系,这是年。去大学报到前还出了个笑话。维修火车头需要经过技术员的批准,否则修理厂不给修。我考大学时,一走就是两个礼拜,我跟工人关系还不错,要修火车头,他们就冒充我签字。结果有一天火车头抛锚,正好停在矿长的门口。矿长出来看,只看到司机,没有技术员,就问怎么回事,技术员跑哪儿去了?司机回答说,(技术员)生病,在宿舍里。矿长还很关心我,专门派人到宿舍来查。这一查就露馅了,宿舍管理员说我回天津了。我从天津回来后,矿长找我训话。他说,两个礼拜的工资得扣掉。我心里想,扣就扣吧,反正我也不干了。离开前,我专门给矿长写了封英文信,大意是说,我已经考上了大学,要回去念书。南下年,我在北洋大学机械系上三年级,林彪带领的第四野战军到了天津,准备南下。为组织成立南下工作团,要征集大学生参军,主要去部队里当文化教员。当年3月我参加南下工作团,所以现在混了个离休。在这之前,长春机场要招收空军,我去报了名。我的身体比较好,一检查都合格,就眼睛近视没过关,最终没被选上。当时我想,大学四年级就是去工厂实习,写毕业论文,而我已经在工厂里干过两年,没啥意思。再说当时毕业就是失业,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我就想到南方跑跑—那时我的父母已经到云南去了,弟弟在北京,就我光棍一人在天津,倒也无牵无挂。南下时,国民党的飞机老来炸,我们就坐火车到武昌。指导员来分配工作,那时分配工作很简单,有个饭碗就行。由于我是大学生,他就叫我去研究室(中南局)。没想到,上午指导员刚找我谈完话,下午又变了,说不行。叶剑英(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到了武汉,要成立南方工作队(后改名华南工作团),去解放广东,要把所有广东人抽出来带走。共抽了3个广东人,我是其中一个,也算是沾了广东人的光。这样我就成了叶剑英的南方工作队成员。由于没有直达广州的火车,我们就坐船、坐汽车南下。年10月1日,我们在赣州开大会,会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家都非常高兴。在赣州没待几天,又坐火车直奔广州。10月14日广州解放,一解放,我们就进城。我当时是个一般干事,部队南下时管大家伙食。每到一个地方,我就买粮、买菜,找房子住店,住店时先拆门板,再铺床,这些事情做得很习惯。进广州后,我被分配到广州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办公厅行政处,当行政处处长的秘书。那时广州市政府还没成立,军管会是个临时架子,没几个人,我所在的行政处就两三人。我整天挎着枪去检查房地产,有老百姓揭发的,也有资本家、国民党跑掉后留下的房产,找到一处,就贴上封条,再移交给市政府。在行政处,我还管到广州来的中央和外国的领导人,其中有个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要随军了解中国解放情况,我记得他叫斯巴诺(翻译名)。斯巴诺从北京带了两个秘书,我陪他上街,一不留神,他插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被扒手扒走了。我马上把这事报告公安局,由于广州刚解放,还很乱,公安局也没法找。年年初,叶剑英所在的华南分局开始着手整顿广州。华南分局党组织管着广东、广西、海南岛、香港、澳门等地区。华南分局第一次开会,就把行政处处长和我抽出来(当时我还不是党员)筹备党代会。党代会由我负责接待。这个会一开完,我和处长就被留在华南分局,相当于现在的广东省委,军管会则交给广州市政府。从这之后到年,我一直在华南分局行政处当秘书。我这个秘书什么事情都管,如苏联的两个空军师要对付国民党飞机,虽然号称是师,实际上就几个驾驶员。我帮他们一起修白云机场,把民用机场修成军用机场。好像是年、年,我还接待了陈赓大将。陈赓要解放广西,就一直往南打。真正解放南方的不是林彪,而是陈赓。陈赓和叶剑英都喜欢跳舞,首长要跳舞,我就去找青年团和妇联,为了可靠,还得审查。他们跳舞时,我管录音机,那时还是老式录音机。我们住在广东的梅花村,原来是国民党大官住的地方,都是些很漂亮的别墅。国民党逃跑后,我们接收过来变成了办公地。那时老有国民党飞机来炸,叶剑英是军人出身,有天晚上响警报,他背着冲锋枪就跑出来了。警卫员说,首长,您别出来。他说,不怕,出来抓特务。当时广州确实有特务,我们也经常出去巡逻抓特务。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央组织部下令:技术干部归队。虽然我早已是不懂技术的技术干部,但在中央“一律不准打埋伏,一律归中央统一分配”的强调下,我也成了归队的技术干部。实际上广东很想把我留下来,但广东没什么工业,有一个新会糖厂。我搞机械的,到糖厂只能当机修工。因为中央规定统一分配,这样,我由北往南,又由南往北,回到武汉办学习班。学习班办完后,又分配工作。因为我学的是机械系,这次把我分到第二汽车厂筹备组(二汽,现在的东风汽车),厂长是刘西尧,原来的湖北省委书记,后来是周恩来的秘书。年3月13日,一汽举行“滁县日”活动,安徽省代表向一汽赠送锦旗。到一汽实习我到二汽时,筹备组不到20人,住在澡堂里。当时二汽把厂址定在武昌的一个地方,年7月15日一汽开工建设,刘西尧说,你们在这里待着干什么,到一汽实习去吧。年8月底,我随一同归队的几个技术干部到了长春一汽,看到的是一片荒野,什么都没有。长春负责接待的人说,我们刚刚选好厂址,正开始土建,你们先到土建总调度室吧。我不懂怎么盖房子,混凝土、钢筋水泥都不熟悉,就马上去新华书店买了不少土建方面的书来学。冬天长春很冷,我们住在小平房里,上班要走一个小时的路才到工地。总调度室人不多,我们主要是跑腿,每天下工地检查施工进度,看吊了几根柱子,吊了几根钢梁,回来向工程师汇报。年年初,施工建设出了一次质量问题,就在现在一汽工具厂的那块地方,靠近中央大道处,有根混凝土柱子没浇好,出现了蜂窝麻面(土建术语,水泥没捣实,像个蜂窝)。工程师想糊弄过去,让工人在面上抹上水泥,这样就看不到里面是空的。工人悄悄告诉了我们真实情况,我们马上报告汽车厂指挥部。饶斌(时任一汽厂长)开大会,提出“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口号,当场宣布把工程师撤掉,表扬了工人,并将这根混凝土柱子推倒返工,保证质量。我曾写过文章描述在一汽的情况,“吃饭当排长,学习当连长,睡觉当团长”。什么意思?人太多,吃饭要排队,所以要当“排长”;学习要联系实际,要当“连长”;我们住在绿园,冬天烧个火墙,还冷得要命,睡觉戴着皮帽子,盖着棉被,把身体“团”起来,所以是“团长”。四五个月后,刘西尧说,你们不能总干土建,还得干点汽车生产工作。一汽成立最早的是工具临时车间,我就到工具热处理车间当生产计划调度科长,当时车间主任是刘清怀。我管了18个技术员,有大学毕业生,也有从北京调来的一些工人。我虽然没当过领导,但比较好学习,又跑到新华书店去买怎么当领导的书。买回来一看,还是这套东西,管人要联系群众。我在党委机关干过,按照那套办法干就完了。又一段时间后,刘西尧又说,你干热处理,还是工具热处理,离搞汽车还有点远,不如先去苏联实习吧。实习前我在俄文班学了七八个月的俄文。教员是个逃到哈尔滨的女白俄,她讲的基本都是生活用语,对技术帮助不大。当时清华大学有本英文、俄文对照的词典,我们就用这本书自学技术用语。作为到苏联的第三批实习生,年4月我和50多名一汽人被派到斯大林汽车厂实习。二汽本想让我学机床设计,但定专业时,工具管理专业没人愿意学,那时候大家都喜欢技术,不喜欢管理。时任一汽总工程师的孟少农就说,让老黄学吧。我是党员,自然要服从组织分配。当时中苏关系很融洽,苏联人看到我们,先问是哪儿来的?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朝鲜人?说是中国人后,就特别热情。举个例子,我们在国内当“排长”,到苏联还得当“排长”,买早点,买面包,都得排大队。我们出国都穿着统一的衣服,苏联人一看,就让我们排前面去,但我们仍然按规矩办事。斯大林汽车厂没有工具处,由一名副总工艺师、工具生产主任领导6个工具车间。其中工具管理有3个车间:工具一车间制造刀量辅具;工具二车间管理工具;工具三车间是夹具和组合机床。另外3个部门是冲锻模车间、模型车间(铸模、木模)和磨具砂轮车间。我在工具二车间实习工具管理。实习老师是车间主任克鲁平诺夫和车间副主任雅库申。车间有经济计划科、技术科、消耗定额科,下属各基本生产车间的工具科和磨刀工部。工具科领导着技术监督工长和工具分发库。克鲁平诺夫教我怎么当车间主任,他在美国福特实习过,实际上也是美国管理方式。他告诉我,美国怎么回事,苏联怎么回事,将来中国发展汽车要两方面都吸收。雅库申教我工具管理业务。我的实习计划是自下而上从基层学起,从仓库工学起,因此接触的人很多,老师也很多。我学过工具分发、基本生产车间工具科长、仓库管理、技术监督,也学过工具消耗和工具定额。这其中就包括很深的技术问题,尤其是工具损坏后要分析原因,是工人操作问题,设备问题还是设计问题。我跟仓库工很熟,跟技术监督工长就更熟了。他们手把手地教我分析工具损坏原因,甚至连工人们如何弄虚作假都告诉我。工具分发工教我如何保证工具供应,送工具到工位;工具科长教我如何制订工具供应计划;定额科长教我如何制定工具消耗定额;磨锋工人教我操作各种磨锋机床。我印象深刻的是工具消耗定额的实习,一般来说这是企业的保密材料。由于实习面广,白天要全面实习,没有时间完成大量的资料抄写工作,我实习的定额科长是个老头,没结婚,他对我很放心,干脆把办公室钥匙交给我,让我可以在夜间抄写资料。这样,我就利用晚上时间,花了3个月时间,把吉斯卡车和吉斯越野车多年来的工具定额历史资料全部抄回来,抄了好几大本。回国后,这些资料对解放车投产起了一定参考作用。由于我是以车间主任(相当于处级干部)身份实习的,根据规定,还可以到莫洛托夫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实习两周。在莫洛托夫汽车厂,我学到了如何设计组织机构。后来一汽工具车间变成工具分厂时,我就参考了莫洛托夫汽车厂的组织机构。和我同车去的还有江泽民。他原来在动力厂,在苏联,他学动力,我学工具。但我们这些实习生都住在一个宿舍里,我和他还同属一个支部委员,我是组织委员,他是宣传委员。在实习期间,还有件难忘的事。年苏共“二十大”,中国派朱德率团参加,会后他到斯大林汽车厂参观。我记得那天我正在车间实习,工具生产主任突然打电话,让我到工具三车间去,向朱德汇报。工具三车间有几台机床是专为一汽制造的,朱德听完汇报后,十分高兴地和我握手。从苏联实习回来后,我被分到工具管理车间(后来改为工具管理科),下面分为定额科、监督科等4个科,我是科长。当时一汽正好出车,我带回来的资料都派上了用场。被孟少农“留”在一汽回过头来说老二汽下马。年,中国有“七汽八拖”,也就是七个汽车厂八个拖拉机厂,到最后只剩下“一汽一拖”—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洛阳拖拉机厂。二汽下马在一汽老俱乐部开会,刘西尧作报告。他说,二汽下马了,从二汽来的实习干部分四股,一股到北边的富拉基型机械厂(简称一重),一股到一拖(洛阳拖拉机厂),一股留在一汽,另有一部分人到国家科委。刘西尧当时是国家科委主任。会后他找我谈话,老黄,你学技术的,跟我到北京吧。我那时年轻,觉得到哪里都一样,就同意去。结果孟少农不干了,他对刘西尧说,老黄这个专业,一汽只有他,他不能走。刘西尧不好再计较。因为孟老总这句话,我就留在了一汽。这一留就是50多年,我的工资也正式转到一汽。年,一汽工具处成立,我是办公室主任。不久,饶斌开始搞班产辆,一厂变五厂—汽车厂原年产量3万辆,班产辆后,一天就是辆,一年个工作日,就是15万辆。饶斌干劲很足,思想也不错。他带了一个小组在底盘厂蹲点,硬是让底盘厂产量翻了五番,达到班产辆的生产能力,还做到了“三不加”(不增加设备、不增加人员、不增加面积)和“三上交”(上交3台机床、3名工人和50多平方米生产面积)。于是饶斌就在全厂推广底盘厂经验,号召大家一起实现一厂变五厂。这样全厂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去。年饶斌调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郭力接任,总厂成立班产辆生产准备处,把我调去当副处长。跟我一起调去的还有张琦(发动机副厂长,已去世)、王达勋(机动处处长,后调任二汽机动处,已去世)、丁方(生产处总调度,已去世)。生产准备处人不多,张琦是处长,我们3个副处长,再加上10多个科长。实际上对于班产辆,总厂党委内也有不同看法。郭力比较务实,他让我们一个分厂一个分厂地查,一台设备一台设备地查,看到底有多大通过能力,以及工人们的干活时间、休息时间,全都得做记录。这样算来算去,班产辆(6万辆)还勉强行。核实完后,我们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总厂。年我到红旗联合办公室负责人事。当时东风、红旗是在机电分厂的一个小角落里干出来的,每个专业厂都设有一块红旗小阵地。厂里要成立红旗车间,我负责从各个车间调技术人员到红旗车间当骨干。这时,大跃进所造成的产品质量问题开始显现。比较严重的有出口蒙古国的辆解放卡车驾驶室后围焊接不牢,影响使用寿命,紧接着是连续生产一年的多辆军用越野车后桥半轴套管法兰盘有裂纹,需要报告军委停止使用。这两起严重质量事故,一个出口,一个军用,在全国影响巨大。从年底开始,全厂开始为时3个月的质量整风运动。要解决质量问题,没有工艺装备就保证不了。郭力对我说,老黄,你回老家去吧。年我又调回工具处任副处长,处长是胡善甫。年胡调到二汽后,我任工具分厂厂长,开始与徐元存第一次搭档。记得有天晚上,监督工长向我报告,变速箱厂当晚一班就损坏了三把工具拉刀,仓库里还剩最后一把,还要不要发?以前我在热处理时,车间主任刘青怀是个老干部,后来调任变速箱厂厂长。我说,没刀子了,停产。刘青怀说,老黄,你不够意思,怎么停产了?一下子报告到总厂,说我破坏生产。这个帽子很大。当时管后方的是总厂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黄一然,后调到哈尔滨工大当校长。他一听觉得不可能,黄兆銮怎么会破坏生产?就把我叫去问怎么回事。我说,变速箱厂一宿损坏了三把拉刀,我还剩最后一把,能不停产吗?对,不能给。黄一然同意了我的做法,批评了刘青怀。监督工长看我支持他们,也很高兴。因为这个事,我在工厂里出了名。年7月13日,国产第一辆解放牌卡车在总装配线下线,当年8月21日第一批解放牌送到北京。工具厂里的春天工具是后方工作,是辅助部门,少不了挨骂,但我这个辅助部门也很光荣,搞生产积极主动,前方有困难,我们就去支援,替总厂担忧。我带着20多个科长,去过铸造,去过前方总装配,去过锻造,跟他们一起解决困难。为了支援铸造,我还把跟我搭档的书记徐元存也“送”给了铸造厂。不仅如此,总厂搞活动我们也积极参加。我本人就很喜欢体育运动,支持工人锻炼身体。体育活动也好,文艺活动也好,什么竞赛我们都是全厂第一,所以工具厂在一汽很有名。郭力很注重管理,找来材料管理、工具管理、质量管理一套书,根据苏联的组织设计,让我们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写书。我写的《工具管理》在一汽档案馆和学校都有,后来汽车厂,包括拖拉机厂都用这本书,把它当成了工具管理书籍的“圣经”。光看书还不行,很多工具厂厂长带着一帮人,专门到一汽来学习。我给他们介绍情况。我说,这是从苏联搬来的东西,你们参考,每个厂情况不同,你们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改造。我这个人群众关系比较好,在“文革”中没受什么苦。“文化大革命”时厂里分成两派,公社派中多数是党员和老工人,指挥部里年轻人较多,革委会要结合干部,这两派都想让我参加。我想,我支持一派,打一派,非犯错误不可,就哪派也不支持,自称是共产党派。包建二汽时,做工具没钢材了,我跑到二汽去求援,找供应处长钱恒珠。他原是哈尔滨的地下党员,“文革”中被隔离。我在宿舍里找到他,他躺在床上,看到我挺奇怪,就问,谁都不来看我,你怎么敢来?我怎么不敢来?我说,管你是真党员还是假党员。然后我说了来意,我们正在给你们做工具,需要高速钢。他说,我现在不管事了,你去找副处长。副处长是从一汽保卫处调去的,我们曾一起打过篮球。我找到他,他说,你放心,我给你解决。组合机车间建立后,我负责买设备。记得有次吊车的长短不合适,革委会就把技术干部批了一通。我说,别批他了,不是他买错了,工厂给的就是这个尺寸。后来就搞了个非标准吊车。年还处于“文革”时期。工具分厂任务很重,一方面要抓质量,保证工具供应,一方面要包建二汽和完成援外任务(援助罗马尼亚建设一个冲模工具厂;援助朝鲜建设一个气门芯厂;援助古巴、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培训实习生等)。由于“文革”中忽视管理和设备维修,工具消耗没有定额,一切为了装车需要,导致各种工具告急。我曾经管过技协,厂里的一些技术大拿我都认识,我就把技协组织起来,让他们挨个攻关。在用人方面,我认为要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此,我提拔过很多工人。梁金成是工具的一个磨工,出身不大好,上海人,因家里亲戚在台湾,长期得不到重用,可他试制的弹性联轴器还打入过国际市场。我顶住压力让他上夜大,推荐他为总厂劳动模范。“丝杠大王”徐天齐,本是个机修车工,技术很高,一般人都干不了的他能干。此外,还有“钳工大拿”陆国铭等。比较有意思的是张国良,后来任总厂革委会副主任,我是总厂副厂长,在办公室我们俩坐对面。他很为难,他说,我工人出身,叫我去处理矛盾,解决思想问题,我干不了。我说,那你去抓技协吧。技协是工会的下属组织,分工时他就去管了技协。工具厂还每年开两次会,我们称为“广交会”,就是广泛地交流技术,大家都觉得新鲜,总厂的技术专家也来参加,干得热火朝天。我接李刚的班再说说解放牌换型的事。为什么换型?当时中央的一位领导说,解放牌老面孔,几十年一贯制。我们还不大服气。解放牌卡车投产后,我们也做过多次技术改进,并在年代着手进行新产品开发,制订过多种换型方案,但国家不投资,不搞改造,最后因资金不到位而放弃。到了年代中期,解放牌卡车的发动机、驾驶室和车头已经十分落后,再加上二汽的东风卡车在市场上的呼声超过了一汽,我们的压力很大,不服气也得换。郭力调走后,刘守华接班。一汽提出了年产15万辆载重车的改造方案,由当时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李刚到北京向时任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作汇报。周子健同意了一汽的工厂改造方案。年年底,刘守华邀请日本的丰田、日产、三菱和五十铃4家汽车公司到一汽考察,历时一个月。这4家公司分别做了评估报告和合作方案。在74栋的汽车招待所里进行座谈时,日本人开价很高,而且还很不客气地问刘守华:你们工厂有钱吗?刘守华也急了,回答说:我是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国营企业,怎么没钱呢?就把日本人给顶回去了。日本人回国前,我们请他们吃饭,用茅台酒招待他们。日本人平时都喝清酒,度数不高,茅台是60度,三菱的总裁是工人出身,他一喝感觉不错。刘守华给我使眼色,让我把他灌醉。我就跟他干杯,连碰两杯,到第三杯时他就到桌子下边去了。他的助手一看不像话,有失外交礼节,连忙把他从桌子下搀起来。他“啪啪”就给助手两个嘴巴,我一看下不了台,赶紧让服务员把他搀回宿舍休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自筹资金,自己开发产品。年,一汽重新上报换型改造方案,年12月得到国务院批准,方案包括换型产品CA型5吨载货汽车年产能6.8万辆,工程总投资2.9亿元,新建面积12.2万平方米,新增设备台。其中换型改造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年年底到年9月)完成新产品开发;第二阶段(年9月到年7月15日),实现新车型全面转产。这期间,由刘守华、李刚带队,组织全厂20人实习团到日本全面考察汽车工业。回来后,在全厂组织学习丰田的生产方式,如看板管理、目视管理、现场5S管理等方法。我们还自己做土机床,代替一些设备,以增加生产能力。年年底,刘守华调任国家机械委汽车局,中汽公司成立后,任副董事长。刘守华走后,李刚接任。没几个月,李刚又调到中汽公司当总经理。谁来接厂长的班?年我到总厂工作后,年8月和李治国、谢云一起被任命为常务副厂长。年1月,一汽成立产品换型指挥部,我是总指挥,副厂长兼总工程师胡传聿是副指挥。3月,中汽公司开会确定我为代理厂长。7月,中组部正式任命我为厂长,我跟徐元存开始了第二次搭档。刚当厂长时,我还办了个厂长学习班。当时分厂厂长都是技术干部出身,少数是专业干部。这个班约20人左右,每周三、周五各用半天时间进行业务学习。我还把各个专业厂的厂长集中起来,有什么困难,哪里卡壳了,哪个职能部门难办了,让他们敞开了谈,同时也让职能部门参会,便于沟通。这个事情后来被时任国家经委秘书长沙叶知道了。沙叶原来是北京内燃机厂厂长,他就把这个学习班办成了个研究会,他是会长,我是副会长,还有其他几个副会长。每年集中起来开一两次会,第一次在厦门,后来在广州、南宁都开过。会议规模近人。这个会也很有意思,郝建秀参加了。她原来是青岛国棉六厂厂长,后来当了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爱人曾志也很愿意参加,她不但参加厂长会,还参加小组讨论会,笔记记得很细,回去后,还把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算是第一手资料。年8月,在一汽运动大会上,徐元存(前排左)与黄兆銮(前排右)为获奖代表颁奖。研制CA当了厂长,我不可能只抓一件具体的工作。当时比较重要的工作是抓换型改造。李治国升任换型改造指挥部总指挥。李治国工人出身,19岁进入一汽机电分厂,当时只有小学文化,后来经过5年业余中学,6年业余大学和1年英语、2年日语的学习,成长为七级钳工。副总指挥是耿昭杰、李中康和王平。此外,有换型改造任务的各专业厂也相应成立换型改造领导小组,副厂长胡传聿任组长。CA由长春汽车研究所设计,这个所在年从一机部划归一汽,后与一汽设计处合并。年10月,在当时的汽研所所长耿昭杰的带动下,对车型和发动机进行设计。CA外形仿的是三菱,当时国家购买了三菱汽车,后来出了些毛病,通过索赔把技术改造费用拿回来了。我们把三菱车头交给汽研所,让他们结合中国情况,改造成中国车头。换型的难点之一是发动机。我们以前做老解放都是汽油机,新车增加了柴油机部分。发动机由冯建权负责,起初他觉得分电盘不好布置。当时他家正好搬新居,他突发奇想,有了搬家的灵感,将分电盘移动位置,既可以在现有的生产线上通过,又可以满足顶置气门的需要,这样解决了发动机问题。柴油机因为排量小,装车有困难。后来我们就在全国找柴油机厂,大连柴油机厂还不错,我和李刚过去谈合作,他们很快就答应了。无锡柴油机厂要价太高,没办法,我们先选了大连柴油机厂。CA量上来后,柴油机不够用,我又带着谢云去无锡柴油机厂。这次厂长换成了蒋斌洪,他原来是江苏省机械局局长,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变成了一汽的铁杆。再后来,这两个柴油机厂都变成了一汽的子公司。换型中间也卡过壳,就是做车身模具。虽然有三菱驾驶室的样子,还得做模子。工具厂加班加点地干,我们还从上海和长春借来一些钣金工,靠他们敲出来。后来这些钣金工都留了下来。CA样车试制出来后,样子还不错,年通过国家鉴定。我们把一部分新车交给哈尔滨,一部分交给新疆,进行道路试验。要说调试过程中的困难那就太多了,发动机有,机械加工也有。厂里的那帮技术大拿就组织起来攻关。新车刚出来,就有段插曲。当时的安徽省省长周子健(后来的机械部部长)想要一些农用车,支持涂县农业。一汽派管销售的副厂长秦懋荣(现为一汽咨询委员会委员)去拜见他。周子健请他吃饭,秦懋荣就问,周书记,安徽要多少车?周子健回答说,我请你吃饭,就两个鸡蛋。什么意思?鸡蛋是圆的,两个鸡蛋是辆,而且他还希望尽快提供。秦懋荣回来报告了总厂。辆等于我们一天的产能,怎么办?当时我在北京参加国家经委组织的企业管理学习班,家里就剩徐元存。徐元存就带头组织“辆CA献工日”。他动员大家支持农业,为安徽省涂县义务劳动。干了一天,辆车出来了,送到安徽省。周子健很高兴,安徽省那时也没钱,就给了我们很多安徽的大米,整整拉了一火车来,厂里职工都分到了这些大米。这期间,我们和二汽也有段故事。二汽最早的产品是我们支援的,二汽的很多骨干都是从一汽过去的。但随着双方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不断加剧,双方逐渐由兄弟转化为对手,甚至还出现过一汽到所包建的二汽单位不让看某些设备的事情。我们跟二汽厂长黄正夏有过多次沟通。黄正夏说,一汽二汽都是国有企业,双方竞争得两败俱伤不好,我们研究一下,搞个联合吧。中汽公司的饶斌和李刚都表示支持。年5月,中汽公司在一汽开“新产品形成能力起步工作会”,我们借这个机会邀请二汽来访。5月3日,黄正夏带着李惠民(原一汽底盘厂厂长,后调任二汽常务副厂长、东风联营公司经理,年11月15日在十堰逝世,享年85岁)、陈清泰等近40人到一汽。经过集体座谈会和分组交流,在饶斌和李刚的见证下,我们双方于5月12日在汽车工人文化宫举行了“友谊互助振兴会”签字仪式。徐元存、我和韩玉麟,黄正夏、李惠民、陈清泰分别代表双方签字。从那以后,每年我们轮流举行一次友谊互助振兴活动。一汽和二汽管销售的、管技术的、管生产的也互相沟通,我们两家关系变得非常融洽。后来东风汽车公司成立后,这种互助活动才逐渐停止。谋求企业自主权为解决一汽的自主权问题,在徐元存的带领下,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当时中汽公司想学国外集中管理汽车厂,像通用、福特以及欧洲的汽车厂那样统一由总部管。当时机械部部长是饶斌,兼任汽车局局长。李刚同意这个方案。刘守华比较客观,他说不行,企业都在地方,不能一下收。他们几个都是一汽老领导,我们对他们很尊重,但关于体制机构问题,我们有自己的看法。作为企业,这样一收,我们岂不是成了小车间吗?何况中国这么大,你怎么指挥?零部件一收,企业要生产,先得找北京供应零件。二汽厂长黄正夏虽然也反对,但他不说话。我们就实话实说,我当时想,万一有什么事,顶多我这个厂长不当了。于是,徐元存、我、韩玉麟,还有工会主席,我们四人联名写信给国家相关领导人,提出希望得到企业自主权的要求。在这之前,薄一波就曾说过,中汽公司不能成为实体,可以像日本的企业联合会性质,管点虚的,实际东西各个企业自己管。薄老一看我们的报告,正合他的思路。最后中汽公司才没有成为实体。年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会议,专题听取一汽汇报,研究解决一汽自主权问题。徐元存、荣惠康、邱文超(一汽办公室主任)和我4人去汇报工作,我做主要汇报,徐元存做补充。在北戴河会议上,我们上交了一个报告。我印象中,包括0辆越野车,辆红旗,6万辆CA,再加上建职工宿舍,以技术改造的名义上报了4.4亿元。结果技术改造只给了0万元,还差很大一个缺口。我们提了一个意见,国家能不能确保一汽2万辆自销权和外贸权,我们用利润来补充一些?否则钱不够,尤其是职工宿舍,老百姓都瞪着眼睛要房子住。对于提到的这些,总理没说别的,倒都答应了。他只对红旗有意见,那时红旗总抛锚,他说红旗质量不行。徐元存说,红旗我们是干一辆赔一辆。当时红旗的确是赔钱,我们是拿着解放养红旗。总理一听,就说,你干一辆赔一辆,干脆就不要搞了。一年搞那么几辆,质量又不过关,有什么意思?这是形式主义。少量用就买嘛!不然人代会要提意见,为了几个领导坐,就搞那么一个工厂。我看英国、法国也坐奔驰车,并没感到什么不体面。不要图虚名而受灾祸。已经定的检阅车可以继续做,做完就不搞了。回去后国务院就正式下文件,停止红旗生产。我们都很着急,红旗不能停产啊!不但职工感情通不过,我这个厂长也很难受。我说,红旗好不容易才搞出来,一下子停产了,怎么弄。当时我还留了个心眼,下令把所有的红旗模具全部保存起来,将来一旦中央要红旗,没有模具,我抠也抠不出来。模具保留了,后来红旗恢复生产才变成可能。话又说回来,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也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后来到财政部当部长。总理同意后,徐元存追问了一句,这些技术改造费找谁落实?知道是甘子玉后,徐元存追着他到厕所,让他盯着帮助落实。甘子玉当场答应了,但回到北京后,除了0万元的技术改造费,其他费用就全否了—财政部拿不出钱。北戴河会议结束后第5天,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就在会议纪要中原则同意一汽进一步扩大自主权的要求,可以在国家计委单立户头。我们担心再出现变化,年10月,我、韩玉麟、葛葆璇等一起去北京,分头向国家计委、体改委、财政部、机械部、中汽公司汇报一汽七五期间技术改造总体方案和0年目标设想。我印象很深,我在北京待了四十九天,住在苏州胡同的一机部招待所。当时找领导很难,我们找到国家计委的一个科长刘志松,但跟他说了没用,这个事还得计委主任定。我们决定找计委第一副主任赵东宛汇报,请他帮助。赵同时也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在中南海上班。一汽在北京设有红旗轿车服务站,服务站的司机进中南海很方便。我们就想了个办法,我、老韩(韩玉麟)等几个乘坐红旗轿车直接闯中南海。门口的警卫员一看我们坐着红旗车,以为是什么大首长,也没问,我们就进去了。我们事先了解到赵东宛所在的办公室,直接把红旗车开到办公楼前,下了车直奔他办公室。秘书问,你们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一汽的厂长,找首长有点事。这个秘书还不错,告诉我们首长在楼上。见到赵东宛后,我们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向他作了汇报,希望他帮助落实。赵东宛是从哈尔滨重型工业出来的,对工厂很有感情。听完后,他说,行啊,这个事情我帮你们疏通。他一点头我们就好办了,国家很快就批准了。一汽终于解决了自主权,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年6月,一汽领导班子换届,徐元存调任吉林省人大副主任,我离休。当年在74栋宣布了两个任命,一是任命我当顾问,紧接着,中组部任命耿昭杰为一汽厂长。年,解放换型到了关键时刻。这年2月14日,耿昭杰在一号门广场召开换型转产万人动员大会,发出了“愚公移山,背水一战,万无一失,务求必胜”的决战动员令。一汽走上了二次创业的艰难历程,后来的历史就交给了耿昭杰。对本文有任何看法,请向下滑动去“写评论”吧! 点击“阅读原文”申报中国汽车企业社会责任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yiqisx.com/yqcj/5733.html
- 上一篇文章: 一汽奔腾T77PRO正式上市售价10
- 下一篇文章: 招募一汽大众品牌经销商招募计划,邀您加